

當前位置:首頁>民俗> 2011年2月24日是什么命(紀念木心逝世十周年)
發布時間:2026-01-22閱讀( 10)

木心被更多人認識的時候,已經是位長者,人們愿意尊他為老師,聽他慢吞吞地講課;后來,他擁有了更多讀者,《文學回憶錄》讓他備受年輕人的喜愛,相見恨晚。但對羨慕張愛玲年少成名的木心來說,自己卻等到79歲,才第一次在大陸出版書籍。最初的《哥倫比亞的倒影》,也沒能掀起閱讀的熱潮,只是本冷冷清清的文學作品,他依然渴望著能被更多人看到。然而,等到讓他成為一種現象的《文學回憶錄》出版時,已經是2013年,那時他已經辭世。
等到他更多的作品出版,人們才意識到,或許對整個漢語寫作來說,他也來得太遲了。那種干凈的、沒有受到上世紀任何文化運動影響的文字,天然地呈現在讀者面前。或許以后,他還有更多的遲到——對他文學觀念的公正評價、對他作品的真正理解、《詩經演》等書籍中耗費的心血、更多尚未面世的遺作手稿、畫作……在現代,他慢吞吞的姿態與社會生活的快節奏格格不入,但也正是這種格格不入,吸引了更多人跟著他的影子,安靜而緩慢地前行。

木心(1927-2011),1927年生于浙江桐鄉烏鎮東柵。本名孫璞,字仰中,號牧心,筆名木心。畢業于上海美術專科學校。1982年定居紐約。2011年12月21日3時逝世于故鄉烏鎮,享年84歲。中國當代文學家、畫家,出版多本著作。
采訪在理想國頂層的辦公室進行,陳丹青和“理想國”的總編輯劉瑞琳正坐在一張辦公桌旁,面前是厚厚一沓《木心遺稿》的清樣打印文件。首批面世的這份遺稿大約共計16萬字,主要是木心晚年時期的筆記、備忘錄和作品草稿,整理工作目前還沒有完成。這只是木心尚未出版的作品的一部分,他還有更多文字,由于沒有留下任何時間、標注,甚至筆跡都無法辨認,暫時無法出版。
在今天,木心幾乎已成為每個讀書人都知曉的名字,但對真實的木心來說,人們了解的,或許連一半都沒有達到。對木心,人們有推崇、有贊賞、有質疑,也有標簽化的誤解。在短暫的寒暄后,我們坐在桌邊,開始在交談中追逐木心在文字中留下的痕跡。交談結束后,這痕跡可以說更清晰,也可以說更模糊。總之就像是他重新在房間里出現了,聽完我們的對話,然后等關于他的話題結束后,就起身拍拍衣服,繼續消失了。

本文出自12月17日專題《遲到的人——木心逝世十周年紀念》的B04-B05。
采寫 | 宮子
對談陳丹青視頻精彩片段:陳丹青談《木心遺稿》修改過程。

《木心遺稿》,木心著,理想國 | 上海三聯書店,2022年1月。
自媒體時代的木心

木心舊照。
宮子:今天我們來,當然主要是紀念木心。你之前每年在木心的紀念日都會寫一些文章,轉眼這么多年過去了,你覺得還有多少想說的沒說出口呢?
陳丹青:他死后五年,我每年為理想國的《木心紀念專號》寫一篇回憶文章。2015年,木心美術館建成了,我又寫過很長一篇談論他的繪畫,放在2016年專號。那是專號最后一期。但2017年又寫了一篇,是倫敦國家圖書館叫我寫的,那年美術館辦了英國文豪的文物展,展品來自圖書館,他們蠻重視,聽說老頭子來過英國,就要我寫回憶,他們翻譯后,放在圖書館網站上。
宮子:每年應該有很多人來找你寫吧?
陳丹青:倒也沒有。情況在變化。十年前知道木心的人很少,2011年他死了,2012年我錄入《文學回憶錄》,2013年出版。那個階段,理想國、烏鎮、我,都想讓大家知道木心。但十年來讀者逐漸增多,好幾個省的民間讀者自發成立了“木心讀書會”。當初我沒想要那么多人知道他,其實大部分人只知道他的名字,記得一些他的俳句,聽過《從前慢》,但果真去讀他的書,畢竟是少數。木心的書不好讀。
實話說,目前許多的讀者是沖著《文學回憶錄》。總之,我跟十年前、五年前的想法不一樣了。知道木心的人太多了,我愿意他還是很小眾的作家。
宮子:你本人現在也象征性地變成了木心的代言人,大家一提到木心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,也有人質疑你是在“造神”。
陳丹青:他死了,然后有了美術館,我又在那兒做事,自然就變成目標啦。但我無法給他代言。代他什么言呢,你說說看?只有一個方便,我做他的事再不用征得他同意了。“造神”,是他們說的,你覺得這是造神么?從2006年木心出書直到現在,都有人在質疑,說我是個托兒。好吧,他們覺得我是個托兒,我就是吧。
我的理解是,木心死去那年,自媒體已經有了。人類從來沒遇到一個時期,有種媒介能讓一個人、一件事,傳播那么快,而且誰都可以加入議論。我跟木心的關系是件小事,可是被放大,被議論了。換在30年前,文學界這個出來了,那個出來了,出版界批評界都做同樣的事,報紙、雜志、研討會、訪談、見面會……集中議論某個作家,但那時不會說你“造神”。自媒體時代就是吃瓜時代,木心不是變成“神”,而是被自媒體變成一只瓜。

《張岪與木心》,陳丹青著,理想國 |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,2019年9月。
宮子:我倒是想起了一個事情,上大學的時候,2013、2014年左右,班上有人期末論文寫了“木心大師”,結果被老師一頓痛罵,說有那么多能寫的當代作家,結果找了個我都沒聽過的什么所謂大師,也不知道是哪門子的大師。
陳丹青:我剛還收到一個00后考生的消息,他說考高中和北師大,試題里有木心的文章,我很驚訝,誰定的考題?他說試題的文學家里有木心,選篇是《童年隨之而去》和《林肯中心的鼓聲》,要學生分析某句什么意思。可是今天你告訴我,八年前有個同學寫了木心,老師會罵,老師沒錯呀,他沒聽說過木心。
錯是錯在哪里呢?就是所謂“大師”。誰說木心是大師?我和出版社從來沒說過,想都沒想過。很簡單,中國有這么多作家,光是我這一輩,50后、60后,出了多少作家?他們的書已經有二三十個國家語種翻譯,歐美都有了專門研究北島、莫言、余華的博士生。現在我推薦一個老頭子,79歲,第一次在大陸發表文章,怎么啦?犯了法嗎,這樣上趕著罵?然后說我是托兒——對,我是,我樂意托下去。
宮子:所以看到有人詆毀木心你都會很生氣。
陳丹青:有三次非常生氣,換到年輕時會上去打。現在變成所謂知識分子,不能動粗了,我們這代人是打架長大的。
頭一個是《三聯生活周刊》的主編朱偉。2006年木心的書剛上架,他就寫了微博,居高臨下,說一堆酸話。他是老編輯,跟我同代,上世紀80年代經手過不少知名作家,大抵是40后、50后、60后。可是看到一個20后,一個79歲的老頭子,頭一次出書,他就這么傲慢、擺譜。木心招惹誰了?實話告訴你,我從來看不起我這一代人,包括我自己。朱偉不知羞恥,跳出來,他本人就是文學編輯,所以十倍的羞恥。
第二個呢,是《羊城晚報》某編輯。《文學回憶錄》出來,他就組織一位姓張的作家寫了文章:《木心:被高估的大師?》,登出來。事后我見了張姓作者,蠻坦率的,他說他當時沒看幾篇木心的文章,沒讀過《文學回憶錄》,他說那個標題是《羊城晚報》編輯加上去的。
最近一次生氣,就是郭文景。說來可憐,他一點不知道自己有多丟人。你批評木心,沒問題,你可以批評任何文學家,批評托爾斯泰或者魯迅,但腔調不要這么難看,話說出去,是你自己的臉,多好的教養啊!
《羊城晚報》后來給《文學回憶錄》一個年度散文獎,叫我去領,我見到了那個編輯,蠻年輕的書生,我就心軟了,我逗他,我說可不可以在頒獎儀式上講這件事情,他馬上慌了,說千萬不要這樣。呵呵,你先撩的事,你躲什么呀——我也是個粗人,常罵街,所以我被罵是活該,但罵木心,我會非常受傷、動怒。
你剛才問我關于木心還有什么想說,有的。針對資深文學編輯朱偉,我有十萬字要說,因為涉及深層的文學是非和歷史是非。看機會吧,目前不會說。
宮子:我覺得木心留下的文字,有一個特點是他太容易被斷章取義了。比如我看《木心遺稿》里面有句“每個女子都應該像清少納言那樣啊”。這話我們都知道就是個人在讀書時隨性的一句感慨嘛,但單獨挑出來,太容易被攻擊了——你什么意思啊,清少納言是日本封建社會貴族階層,她身上多少社會約束,讓每個女子都像她那樣,這不是和現代女性的個性解放唱反調嗎?我覺得這個時代,人們似乎無法容忍一個人去隨性感慨,你說的每句話都要負責任,都要有依據。
陳丹青:這就是自媒體時代,大家都能說一嘴。但現在的好處是,留言意見正反面都有,一個人被修理慘了,會有人出來說話。
宮子:那劉老師作為出版人,從出版《文學回憶錄》開始就有預料到木心在今天受歡迎的程度嗎?
劉瑞琳:最開始是2006年的《哥倫比亞的倒影》。那是木心書的簡體字版第一次在大陸出,立刻有人覺得他很有意思,后來作品一本一本地出,讀者越來越多。《文學回憶錄》是2013年出的。

木心在紐約授課。
宮子:當時他還在世,知道這個事情后有什么反應呢?
陳丹青:你在遺稿里會看到的。回國后他寫了很多感想。第一,很高興有讀者了,第二,感慨名聲來得太遲,反倒懷想默默無聞時。當他發現有名了,百感交集。
宮子:他好像很渴望能有人來寫一寫他?
陳丹青:是的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跟他一起玩,隔三差五他就拿著稿子給我看,我說寫得好啊,之后越來越熟,他說你將來要寫啊。但我不肯寫,寫了,他肯定不會滿意的。他對什么文字都不滿意,包括他自己的。結果他死后我馬上坐下來寫,寫完會難過,因為他看不到了。他活著時我寫過一篇,就是2006年木心大陸版第一次推出的時候。
木心的“孤獨”與“通透”

木心舊照。
宮子:但現在變成研究他的人太多了。我很好奇,不知道如果他還活著,看到這么多人研究他,寫他的論文,會是什么反應。因為我覺得,藝術家、作家可以很極端地分成兩類,一類是需要在研究里活著的,另一類呢一碰到研究就死了。
我覺得木心就是后面一類,野外的,如果把他抓到書桌上研究、剖析,他就死了。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他看到這么多人研究他,他會不會重新躲起來。
陳丹青:哈哈哈,你很敏感啊!2014年上海圖書館舉辦《文學回憶錄》的活動,上千人參加,有位嘉賓是浙大教世界文學史的張教授,發言一開始就說得很妙,他瞧著整個大廳坐滿人,說:木心要是看到,一定會說:“不對的,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。”他說的非常對。
木心遺稿里有句話,說是做墓志銘:“不要寫我,你們寫不好的”。可是你不要信他。他很希望人家研究他,理解他,他最信賴的學者叫童明(劉軍),是加州大學教西方文學、研究尼采的,他們倆交談了好多年,眼下他也真的在做,但他要教書,時間少。我們還在等他把木心的專題研究做出來。
可是各大學的年輕人早已寫了不少木心研究論文,碩士的,博士的,我都看不過來。專門的木心作品研究會前幾年也成立了。最讓我驚訝的是,有三個人,完全業余,自行釋讀《詩經演》,因為最難懂的是《詩經演》,我們不知道該怎么辦。有個人做得特別好,是位干部,退休后花了五年時間,一字一句釋讀,這應該算是研究吧?

《詩經演》,木心著,理想國 | 上海三聯書店,2021年4月。
宮子:他晚年的時候據說是如果看到有人寫他的文章,他會記下來,他會看……
陳丹青:沒有一個藝術家不希望別人看他。沒有的。張愛玲從來不回復讀者,但每篇評論都看。藝術就是為了跟人分享,為了拿到窗外去——來看呀,來看呀,告訴我你們怎么想。沒有一個藝術家會說:“啊,我才不想知道讀者怎么想。”那樣說是不誠實的。我不太相信作家關于自己的談論,不要太相信。
宮子:有時讀他像“藝術家哪里是要隱退啊,他是等著你來找他啊”這樣的話,會感覺這些看似俏皮又矯情的話語背后,其實不知道隱藏著多少辛酸和孤獨。我覺得木心是個孤獨的人。
陳丹青:你能看到這一層,不容易——你覺得你孤獨嗎?
宮子:還好。
陳丹青:還好?那你牛啊。我聽太多90后80后跟我講,他們孤獨得一塌糊涂。問題是,很多人感慨木心孤獨,是的,他當然孤獨,但說木心孤獨,什么意思呢?
宮子:他的這種孤獨也是在遺稿里看到,他有一句話,就和讀者說不要輕易去看破紅塵,看破紅塵容易,但補回來就難了。
陳丹青:你怎么理解?我不太懂這句話。
宮子:可能首先一點就是,他太通透了,他太了解人性了。就像一個心理學家——這個世界上最沒辦法解決自己內心癥結的人是誰呢,就是心理治療師自己,因為他們太明白問題出在哪里了,所以根本無法給自己治療。我覺得木心也是這樣。
陳丹青:還是沒明白你的意思,不過我同意,如果一個人看破人性,太通透,對創作未必好。以我了解的木心,他沒認為自己通透。他有很多困擾,他經常犯傻,他在遺稿里寫了自己的傻。他寫小時候是全烏鎮最無能,最沒前途的人,什么都拿不出來。他不知道和我說過多少次,說年輕時太傻了,不會說話,不會做人,什么作品也沒有,他很晚才建立自信。
宮子:這可能是“通透”帶來的另一個壞處。有時候去創作一個東西,寫小說,或者畫畫,最好的那部分幾乎都不是創作者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干什么,而是近乎一種出神或無意識的狀態,寫東西的時候可能自己都預料不到之后會發生什么。但木心有些太懂藝術了,看他在《文學回憶錄補遺》里提到一小段自己寫的東西,很清楚地知道該如何開頭,如何按照中國傳統的方式破題,接下來又該如何順承。這對創作來說并不是個好事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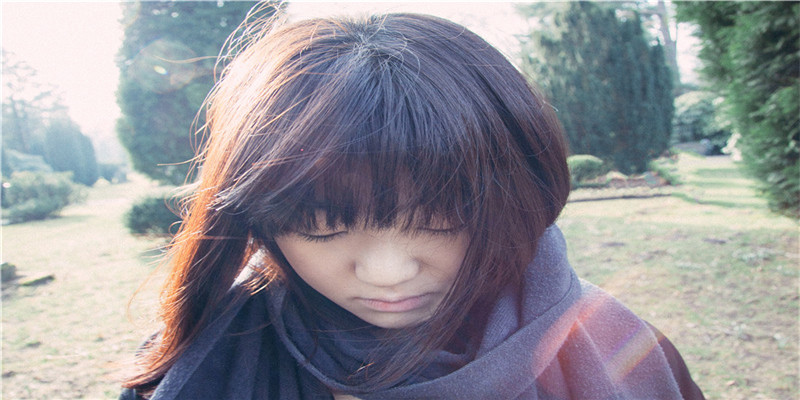
木心手稿。
劉瑞琳:我好像有點理解你的意思,是說木心他太明白怎么樣去寫了,看得太透了,所以會影響他的寫作。可能木心說的那句紅塵看破了就補不回去了是這個意思,是吧?
陳丹青:有可能啊。不過我不認為這會影響木心創作,但會影響他寫長篇。魯迅和木心一樣,太銳利,不適合鴻篇巨制。別人攻擊魯迅寫不出長篇,只會寫短的,魯迅蠻生氣的,寫了雜文懟回去。但他是想寫長篇,寫楊貴妃,沒寫成。他跟木心是一類人,智性太高,看透。寫長篇必須很傻,像個螞蟻慢慢爬。木心曾說:喔喲!寫長篇需要巨大的人格。
劉瑞琳:這是不是也是木心先生一直沒有寫出長篇的一個原因,他一直有這個計劃。他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有一個大本子,他就很明確這個大本子要用來寫《瓷國回憶錄》,然后只寫了開篇的一部分。
陳丹青:對,這個長篇的開頭現在還沒找到。他念給我聽過,然后沒下文了。魯迅,木心,都寫不出長篇。這和通透有沒有關系,我不知道,曹雪芹也通透啊,但他寫出了那么長的《紅樓夢》,長得要命。木心說起曹雪芹,說起陀思妥耶夫斯基,說起哈代,就很吃醋的樣子,我相信魯迅看到《紅樓夢》也吃醋的。
但我一點不認為木心和魯迅非得寫長篇。長篇是爬行動物的事,木心和魯迅是飛掠的。世界上已經有這么多好長篇,我不會在魯迅和木心那里尋找托爾斯泰給我的快感。
木心的拙與傻
木心舊照。
劉瑞琳:我們第二次去看他的時候,他晚上請我們吃飯,講了兩件事情。一個就是他要寫一本書,《讀者》,這個他也說了很多遍,而且第二天早上還和我們說“我昨天晚上已經開始寫了”。另一個就是《瓷國回憶錄》。其實他到最后已經沒有力氣寫了,但這就變成他心里一直惦記的兩件事。
陳丹青:當然,他老想做他做不到的事情,哈哈,這就是傻呀。
劉瑞琳:不過他剛才提到的一點讓我很好奇,他剛才說看了木心的遺稿,感覺還是那個熟悉的木心。但我看了后感覺不是之前發表的那些作品里的木心了。
陳丹青:你在他的書里會看到一個極其機智的人,精巧,講究。但他遺稿中的一半內容,非常率真,老實,不打磨,直話直說。你會發現另一個木心。
劉瑞琳:所以我很想聽聽你的看法,因為你現在是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。
宮子:我認為還是之前那種熟悉的木心,包括他之前發表的作品,像《文學回憶錄》,我也認為那里的木心是一個笨拙的木心,而不是機智。因為經常讀到他評論一個小說,會說類似于好得說不出話來,讓人想眼淚汪汪之類的話,就像個嘴笨的人想夸一個東西好但又說不出多余的話來。這些絕不是一個聰明的評論者會寫下來的句子,聰明的評論者不會那么完全地把自己暴露在讀者面前。我認為這反而是木心的一種笨拙。
陳丹青:那你很厲害啊。木心其實很憨的,甚至很傻,真正精明的人不會這樣說話。我喜歡他就因為他矛盾,復雜,多面,而且懂得怎樣展示他的多面。他在已發表的文字里步步設防,但另一面,他整個兒寫作又是不設防的,極端個人的,根本不考慮外界。所以他在七十年代會受罪,他就是個書生,危險到門口了,他還在想他的詩。
宮子:而且這一定是個過程,想兼顧通透和世俗,倒是容易的,但一旦達到了徹底通透、看破紅塵的狀態,再回去就難了。
陳丹青:哈哈,好像你特別在乎看破紅塵這件事。
劉瑞琳:年輕人好像很愛說這件事情。陳老師你覺得你現在這個年紀看破紅塵了嗎?
陳丹青:沒有。“看破紅塵”這句話就是沒看破的意思。生命就是紅塵,除非你趕緊死,不然你就沒看破。從字面意義上,所謂“通透”要到木心的年齡段,要經歷很多事情,但木心要看破的是“宇宙”。遺稿中有句話,大意是人類想破解宇宙,不自量力。他出語毒辣,很會“損”,“損”一切事物,“損”各種人,包括“損”他自己。我反而覺得這是他的孩子氣,絕頂聰明的孩子,嘴很毒的。

《文學回憶錄(1989-1994)》,木心/陳丹青著,理想國 | 上海三聯書店,2020年7月。
宮子:可能這個話題牽涉到的另一個問題,就是木心他是如何看待“人”的。很有意思的一點是,讀木心能發現,他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名言的反面——愛具體的人,不要愛抽象的人。感覺在他眼里,遠處的人、藝術的人、抵達不到的人,甚至散文里路邊萍水相逢的小攤小販,遠遠望去,都那么可愛;然而現實的人、具體的人,一走近了,仿佛便丑陋了。
陳丹青:哈哈哈,你再多讀。多讀了你會發現他說過同樣的意思。你會發現他在同一個問題上,有這個意思,也有那個意思,他會有很多說法,而且在其中享受快感。
宮子:是啊,他是個沒有固定體系和邏輯的人。有時候看,會心想,哪怕你有個什么流派,有個什么主義呢,但凡隨便有一個,就有相應的圈子,當你受到攻擊的時候就會有人站出來替你說話。但那,就絕不是木心了。
然后,再說回到他“孤獨”的話題上。你在美國剛認識他的時候,試過幫他賣轉印畫,可惜大部分人不識貨,是嗎?
陳丹青:有人識貨,但覺得不好賣。他被拒絕的經歷非常多。但這不是要點,跟他的孤獨沒有太大關系。很多作家如果你問他是否孤獨,我相信各有各的孤獨。他跟我們,也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有作家相比,最不一樣的是,他被外界知道是最晚的。王安憶跟我是同屆,出名時也就二十七八歲。阿城比安憶大一點,出名時35歲,在那代人算是晚的,我不知道60后作家出名時多大歲數,但是你可能找不到一個當代作家,79歲才在大陸第一次出書。他在臺灣發表散文,早一點,也快60歲了。這是木心跟所有作家——且不說寫得如何——最大的區別。
宮子:那他在美國如何謀生呢?
陳丹青:起先是稿費。好幾張華人報紙在紐約,他投稿,同時在臺灣出書,有版稅。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他也賣畫,能維持體面的生活。遺稿里有他的賬單,差不多等于收入表,每篇文章多少字,多少稿費,他會記,有點像魯迅,喜歡弄小賬單。

木心畫作。
宮子:二位應該都參加了他的葬禮。葬禮上播放的不是尋常的哀樂,而是古典樂。這是他留下的遺愿嗎?
陳丹青:不是。他沒留下任何遺愿。他發昏了,譫妄了,然后死了,沒有一句話留下來。但是第一,他和我都喜歡古典音樂。第二,當時就這么做了。12月24日是葬禮,22日晚上我放CD一個個聽,然后選出來,排了順序,請烏鎮一位錄音師在音響里事先準備好,比較長的那段在靈堂放,短的那個音頻在葬禮上放。
宮子:他還有在“文革時期”留下的音樂手稿,還有筆記《獄中手稿》,這些都還能找得到嗎?
陳丹青:《獄中手稿》的三分之一在美術館陳列。你有興趣可以翻《木心紀念專號》,有五篇被他自己強行解讀出來,因為字跡只有米粒大小,一個擠一個,很難辨認。他不認為《獄中手稿》有解讀價值,只有觀看的價值。他說他再不能那樣寫作了。音樂手稿都在,大概40份。其中有六七個譜子被年輕音樂家編創為可演奏的譜子,2016年演奏過。

《木心紀念專號》,劉瑞琳主編,理想國 |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,2013年1月。
罵聲的泛濫與批評的空白
宮子:另外借助木心,其實也可以反思我們現在的很多事情。比如對木心的攻擊,斷章取義地讀到其中一兩句話就開始罵,這是不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對審美的包容性也越來越小?
陳丹青:如今每個用微信微博的人都不被包容,不是嗎?你說他的話太直白,金句又多,太容易被人挑出來。是的,但也不是。自媒體時代的言論其實都被轉發、被曲解、被攻擊,這不是木心一個人的遭遇。我是覺得,誰質疑,請寫出來,說明他讀了木心,注意到他,甚至在乎他,然后很多質疑,很不以為然。很好啊,寫啊。
要罵,沒人攔得住,譬如郭文景。但罵有罵相,別弄得太難看。罵和質疑是兩回事,質疑就是批評。我非常渴望中國多一些文藝批評,文學的,音樂的,繪畫的,有嗎?誰要是長篇大論告訴我:木心不行啊,他的觀點、寫法,他所謂的美文,根本不行啊,然后我看了很被說服,那我會高興,說明還有認真的人,愛文學的人,說真話的人。
有嗎?你告訴我。大多是粗鄙的,東一句西一句,吐口水。這么多年了,看不到認認真真的批評,哪怕千把字短文,駁斥喜歡木心的人,看高木心的人,而且言之成理,那我會非常高興中國又出了個人。
這樣一個話語環境,木心干凈,確實討人厭。可是誰看過木心的書,誰真的喜愛他,一聊就知道的。尤其是年輕一輩,心思很干凈,很誠懇。六年來我親眼看到來很多青年讀者,每周收到木心讀者的信,什么感覺?大多是很文弱,很內向,很淳樸的人,迷途羔羊似的。他們未必真懂,可是為了木心哪句話,誠心誠意老遠來烏鎮,展廳待很久,來好幾次,還會哭。
當然,很多游客是為了蹭空調,拍照,那也好啊。美術館就是讓人來逛來玩的。
木心留下的追憶與反思

木心舊照。
宮子:是的,年輕人中喜歡木心的很多,而且很純粹。我忘記是誰說的了,在中國不會有人讀了莫言的書就想去見見莫言這個人,但是讀木心的書會。
陳丹青:梁文道說的。他說一個魯迅,一個張愛玲,一個木心,人們讀了他的書,還想見這個人。我不能說沒有其他人,但這現象是很奇怪。今年還有人給木心寫情書,字跡娟秀,“我愛你”。每次看見有信,以為是給我的,一打開,寫給木心。當然這是少年期的心理投射,我相信每個中國作家都收到過不少情書,區別是,木心已經死了呀。
剛才你說的那個考試寫木心的同學,我關心他后來做什么了。少年人容易喜歡木心,真正讀書,相信書,都是十來歲的事。眼下00后讀者也出現了,他們在喜歡一個至少爺爺輩的人,但未必會喜歡自己的親爺爺。他們真的愛木心,我很奇怪。
宮子:我是來到書評周刊做編輯了。不過,木心很多時候也讓我反問自己。假如我收到了一篇木心那樣的書評,里面說一本新出版的小說——“寫得真好,好得像是一個人在笑的時候眼淚汪汪”,我會給它發表嗎?這是我經常反問自己的一個問題。
而且就像你之前在一期關于凡·高的視頻里說的,每年看藝考生的畫,那個技巧給凡·高一輩子他都畫不出來,但那些畫你看了,就很想死。我有時收到的書評也是,邏輯觀點特別充分,論證很完整,但我看了,也想死。我去798藝術區,看展覽,看作品旁邊的那些展語,也想死。
陳丹青:你今年多大?27歲?好吧。等你37歲、47歲,不要變成他們。你要知道,他們年輕時恐怕也跟你一樣,也對上代作家的文章嗤之以鼻,結果漸漸變成你說的這種,職業批評家,職業教授,然后給一個20后讀到了,想死。
宮子:所以我們今天會紀念木心,也是因為像這樣一個人,那樣的一個干凈的世界的人,他離開了,而且離我們越來越遠,再不會有這樣一個人再走回來了。

木心舊照。
劉瑞琳:從他的作品集到《文學回憶錄》,再到現在這個《木心遺稿》,我越來越覺得木心是一個特別可愛、有趣的人。我也很難說清楚他究竟是怎么樣的,但他的那些話別人是說不出來的,就是沒有這種人了。馬上要出《木心遺稿》,我心里會有點不安。經歷了幾次木心的書出版后,有很多人喜歡,也有人要罵。就是一方面總有人在非議,另一方面總有讀者在催問,怎么還不出、怎么還不出。
宮子:我倒是覺得無所謂,做書嘛,把書給到喜歡的讀者手里就好了。博爾赫斯的全集一輯兩輯三輯地出,難道每本都好嗎?里面有多少是他給阿根廷報紙寫的用于謀生的邊角料啊。馬爾克斯和石黑一雄,連演講都要給他們做成書,真有這個必要嗎?所以我覺得只要有一部分讀者真心期待就好了。
陳丹青:再說一個《木心遺稿》的事。他寫了好多人名。我分辨了,其中部分是他上海美專所有同學的名字。部分是他工藝美術工廠,就是他遭罪的單位里幾乎所有人的名字,非常長,還有就是他家人,包括傭人一共18個。有兩個原因,一個是老了,他在回想,他再也見不到他們了,都死了,老了。80歲前后,他開始回想這些人。而且這種回想非常真摯、樸素,連名帶姓,一個個寫下來。我做不到,我不會回想全班同學的名字,而且寫出來。
還有一個,他在練記憶力。我認識他時他比我現在還年輕,快60歲了,我們聊天常想不起某個名字。他說,保持想,直到記起來,這樣會鍛煉記憶力。他真的這么做了。
采寫 | 宮子
編輯 | 宮子、青青子、羅東
校對 | 薛京寧、李銘
Copyright ? 2024 有趣生活 All Rights Reserve吉ICP備19000289號-5 TXT地圖HTML地圖XML地圖